安德烈:妈妈,我来了香港

- jclwone LV.旅长
- 2017/9/3 17:19:53
妈妈:
我来了香港,你却又去了台湾。我猜你一定很好奇我的港大生涯。
几乎一天之内就认识了一缸子人,不过全是欧美学生。你只要认识一个,就会骨牌效应般认识一大串。第一天,见到一个高个子,蓝眼睛金头发,是奥地利来的约翰。他直直走过来,问我要不要去浅水湾游泳。到了浅水湾,海滩上已经有十几个人横七竖八躺着,在晒香港的太阳。一发现我会讲德语,马上就有几个德语国家的同学围来。他们是奥地利或德国或瑞士人,可是都在外国读大学——荷兰、英国或美国等等,然后来香港大学做一学期的交换学生。
好啦,我知道你要啰嗦(我太了解你了):喂,安德烈,你要去结交香港本地生,你要去认识中国学生!对啊,可是很难。
国际学生自成小圈圈,并不奇怪。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接触亚洲,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摸索。就拿有名的香港小巴来说吧。没有站牌,也没有站,你要自己搞清楚在哪里下,最恐怖的是,下车前还要用广东话大叫,用吼的,告诉司机你要在哪里下车。国际学生就这样每天在互相交换“香港生存情报”。我比他们稍好一点,小时候每年跟你去台湾,对亚洲好像比他们懂一点,但是懂一点跟“泡”在那个文化里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没有真正在这里生活过,我也只能是一个旁观者,从欧洲的角度。
国际学生跟本地生没有来往,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语言障碍。港大的所有课程都是英语教学,所以你会以为学生的英语一定是不错的。告诉你,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我发现,很多学生确实能读能写,但是,他们讲得非常吃力。大部分的学生不会用英语聊天。最吃惊的发现是,香港学生可能可以用文法正确的英语句型跟你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什么东西,但是,你要他讲清楚昨天在酒坛里听来的一个好玩的笑话,他就完了,他不会。
但是你也不要以为国际学生就是一个团体,才不是。里面还分出很多不同圈圈。譬如说,美国和加拿大来的就会凑在一起;欧洲来的就另成一个小社会。你可能要问,是以语言区分吗?不是,因为我们——德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在一起聊天,也是讲英语。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比语言更深层的文化背景造成这种划分 ——你很自然地和那些跟你成长背景接近的人交朋友。美加来的和欧洲来的,差别大不大?我觉得蛮大的,虽然那个区分很微妙,很难描述。文化气质相近的,就走到一起去了。
表面上,这里的生活和我在德国的生活很像:学科跟时间安排或许不同,但是课外的生活方式,差不多。功课虽然还蛮重的——我必须花很多时间阅读,但是晚上和周末,大伙还是常到咖啡馆喝咖啡,聊天,也可能到酒吧跳跳舞,有时就留在家里一起看电视、吃披萨,聊天到半夜。
有语言,没有交流
你问我愿不愿意干脆在香港读完大学?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两个月下来,发现这里的生活质量跟欧洲有一个最根本的差别,那就是——我觉得,香港缺少文化。
我说“文化”,不是指戏剧、舞蹈、音乐演出、艺术展览等等。我指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情趣。
用欧洲做例子来说吧。我最享受的事情,譬如说,在徒步区的街头咖啡座跟好朋友坐下来,喝一杯意大利咖啡,暖暖的秋天午后,感觉风轻轻吹过房子与房子之间的窄巷。

- 应无所住
- 2017/9/3 18:23:20
美好的并非只是那个地点,而是笼罩着那个地点的整个情调和氛围,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的沉淀。
酒吧跟咖啡馆,在欧洲,其实就是小区文化。朋友跟街坊邻居习惯去那里聊天,跟老板及侍者也像老友。它是你的“家乡”跟“文化”概念里很重要的一环。香港却显得很“浅”——不知道这个词用得对不对。这里没有咖啡馆,只有蹩脚的连锁店星巴克和太平洋咖啡,要不然就是贵得要死其实根本不值得的大饭店。至于酒吧?酒吧在香港,多半只是给观光客喝个毙掉的地方。还没毙倒在地上的,就歪在那里瞪着过路的亚洲女人看。一个典型的兰桂坊或湾仔酒吧里,人与人之间怎么对话?我写给你看:
酒客甲:乐队不烂。
酒客乙:我喜欢女人。
酒客甲:我也是。
酒客乙:要点吃的吗?
酒客甲:对啊,我也醉了。
酒客乙:乐队不烂。
酒客甲:我喜欢女人……
吧啦吧啦吧啦,这样的对话可以持续整个晚上。人与人之间,有语言,但是没有交流。
永远在赶时间
我还发现,香港人永远在赶时间。如果他们在餐厅、咖啡馆或者酒吧里会面,也只是为了在行事日历上面打个勾,表示事情做完了。这个约会还在进行,心里已经在盘算下一个约会的地点跟交通路线。如果我偷看一个香港人的日历本的话,搞不好会看到——09∶15-09∶45跟老婆上床,10∶30置地广场,谈事情。每一个约会,都是“赶”的,因为永远有下一个约会在排队。好像很少看见三两个朋友,坐在咖啡馆里,无所事事,只是为了友情而来相聚,只是为了聊天而来聊天,不是为了谈事情。
我有时很想问走在路上赶赶赶的香港人:你最近一次跟朋友坐下来喝一杯很慢、很长的咖啡,而且后面没有行程,是什么时候?
搞不好很多人会说:唉呀,不记得了。
人跟人之间愿意花时间交流,坐下来为了喝咖啡而喝咖啡,为了聊天而聊天,在欧洲是生活里很大的一部分,是很重要的一种生活艺术。香港没有这样的生活艺术。
国际学生跟本地学生之间没有来往,会不会也跟这种生活态度有关呢?
安德烈
亲爱的安德烈:
对我最重要的,安德烈,不是你有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而在现代的生 活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第二,它给你 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 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至于金钱和名声,哪里是快乐的 核心元素呢?假定说,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 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 理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庸”。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 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当你的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 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我怕你变成画长颈鹿的提摩,不是因为他没钱没名,而是因为他找不到意义。 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 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如果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名比利,而只是在为自己找心灵安适之所在,那么 连“平庸”这个词都不太有意义了。“平庸”是跟别人比,心灵的安适是跟自己 比。我们最终极的负责对象,安德烈,千山万水走到最后,还是“自己”二字。 因此,你当然更没有理由去跟你的上一代比,或者为了符合上一代对你的想象而 活。
MM

- astan
- 2017/9/3 21:08:45
《亲爱的安德烈》,这本书也是我儿子学校推荐的书单,目测他还没看,我已经看完了。

- aa123456aa
- 2017/9/3 23:05:56
室友和他选了同一门课,还分在一个group,却不知道他就是龙应台的安德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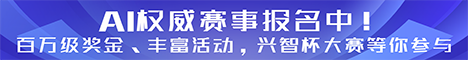
 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